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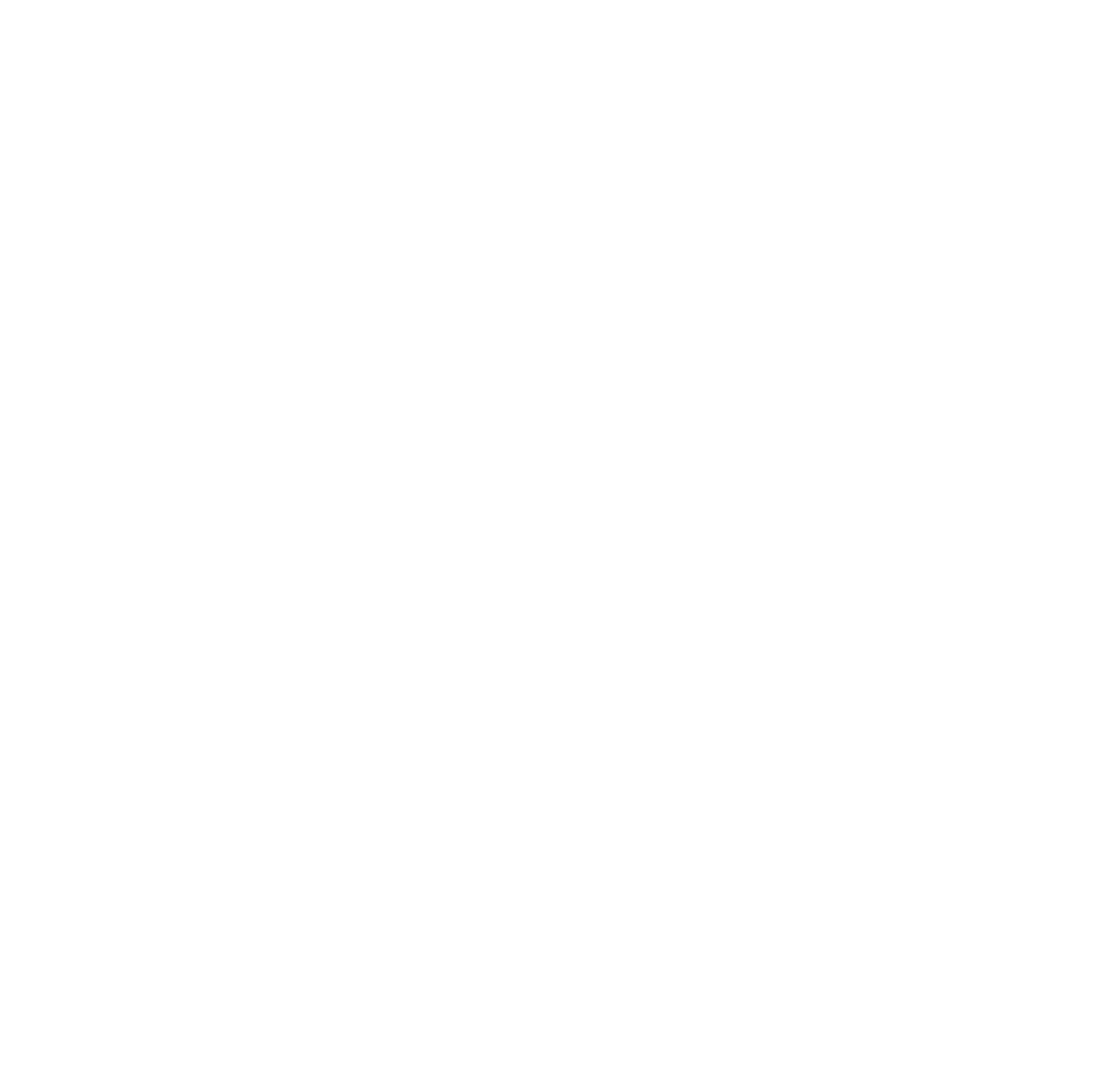
分享:
文/高敬賢
逢甲大學建設規劃辦公室主任
建築專業學院助理教授
建築的生命性及生成過程
逢甲大學共善樓,從2018年與隈研吾建築都市設計事務所(KKAA)開始發展概念,邁入設計階段,經歷疫情及物料價格瘋狂飆漲,兩年半的緊湊施工,自年初啟用至今,與共善樓經過了一個學期及一個暑假的實體相處,我們好像還在彼此相互認識更深的進展:有很熟悉幾乎視之為當然的;有持續發掘的潛力;有意想不到的體驗;有事與願違的使用情況;也有設計意圖被「歪樓」的詮釋的good and bad(非幾何結構的歪)。如此打開話匣,定調是將共善樓的角色設定為有生命的,從如何的生成,如何成就當下,如何持續變化消長。引述我們逢甲團隊助理蔡少甫以共善樓作為研究對象的碩士論文:「建築常被以無生命觀點或建築師一人看待。但是建築的生成過程非私我的活動,是眾多行動所相伴連結,因不同階段的生成而形成自己的表述,參與者因而在活動中成為建築自身整全價值的因素。因此對判斷主體的了解與定位固然重要,而萌生「自身」的覺知,成為建築生成行動中的實踐圭臬。」此刻分享的焦點不是在「建築物」的「物」,著重於技術性相關分享,我們有機會再聊。
從20多年前水湳經貿園區總體規劃階段,逢甲大學楊龍士榮譽資深副校長代表校方,不遺餘力奔走,於2012年提出購地計劃,2018年取得位於中央公園裡的學術綠廊毗鄰逢甲校園5.7公頃的文教用地。對於這一片土地未來的想像,一路嘗試數回的可行性研究與推敲,其實都沒有定論,沒有拍板。
我們究竟想要成就什麼?
大學校園裡的新建築,應該蓋什麼?
許多答案是透過近乎反射動作的定性定量思維:教室、討論室、行政及教學辦公室、實作場域、展覽空間、產學孵化研發、圖書館、社交空間、停車場、餐飲、實習商店、校友會館、校史館(還有包括建築學院搬遷的謠言)⋯⋯不論上述是「名詞」還是「動詞」,不論是從「需求端」還是「供給端」出發,套路都是構思的「習慣」。直到2018年,順利取得土地,我們迫切需要誠懇面對如何實踐。我們實踐的故事,是要超越一棟樓宇。起點是這一個始終的共識,嗅得到企圖和高度,但是籠統。
我們究竟想要成就什麼?
大學校園裡的新建築,應該蓋什麼?
面對反復出現的問題,逢甲大學高承恕董事長回應:「人類生而不自由、不平等,但我們可以改變!教育一定是要樂觀的,沒有熱情的溫度,就只剩下重複的工作。孩子們都年輕,在大學的歲月裡,應該是生動活潑的日子,不論是什麼背景、來自何方,都有機會、都有盼望。這是我們想做的而且能做的事,多一點自由,更接近平等,於是在平凡中就會有人性的尊嚴!能做的事總是有限,卻也無窮;永遠在理想與現實中擺盪,這也是奮鬥的趣味與熱情之所在。」這一段成為共善樓的故事和啟示。

共善樓成長背景
緣分
故事裡重要的角色,Kuma Kengo隈研吾先生,也真的是緣分。感謝當時任教於逢甲建築的加藤義夫老師與隈研吾先生私交深遠,2015年邀請隈研吾先生第一次造訪逢甲大學演講,日後每年至少造訪逢甲一次,參與國際工作營,演講分享,2016年於逢甲建築專業學院成立時,曾與夏鑄九老師精彩對談。每一次的見面相處,和逢甲越來越投緣,對於逢甲的辦學及校園場域的品質與氛圍都很認同;對於逢甲大學的都市環境,我們「夜市大學」西側銜接有機生成的都市紋理,東側新校地屬於全新規劃的水湳經貿園區,充滿趣味和生活的涵構,甚感興趣。校方欣賞也認同隈研吾先生「負建築」核心思想與作品及實驗的實踐姿態。隈研吾先生對於哲學和社會學的鑽研,又與逢甲大學高承恕董事長社會學的背景產生共鳴,餐桌上暢談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學者,Jürgen Habermas尤根·哈伯瑪斯。
我們珍惜每一次學術層面的交流互動,感謝隈研吾先生的賞光,從來沒有想過會有可能成為甲方乙方的關係。直到有一天高承恕董事長在校內會議提出想邀請隈研吾先生參與水湳校地的規劃設計的想法。由於本人是與隈研吾先生事務所的聯絡窗口,就希望我能代表校方,徵詢隈研吾先生意願。當時面帶微笑「呵呵」兩聲回應,心想著機率渺茫。一所臺灣的私立大學,想找國際一線的建築師⋯⋯好吧,反正問問也不花錢,就問吧。隈研吾先生竟然欣然答應。奇妙的緣分,進入了另一個層次,奇妙的旅程,就此展開。還記得第一次和隈研吾事務所的會議是在2018年4月1日,沒錯,愚人節,but this is no joke.
規劃與建築概念發展的過程,總括校方的要求:
留白
這是最早提出的方向。留白,不要蓋滿。也是面對少子化的大環境,往後學生人數不會增加,空間不是不夠用,所以新的空間場域不是為了生出更多樓地板面積,而是宣言、是價值觀、是體驗、是生活、是記憶,同時帶動整體校園的改動,改變對於場域的認知。留白是為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想像。「量」有透過容積建蔽率詮釋,空間跨XYZ三個軸向的留白;空間意境的「質」,也有留白的美。往後的設計,留白產生也成就了一系列光譜,空間的虛實與連接、人為與自然元素的比例、私密與公共、規模的變化、視覺的穿透、時間單位(從一天內的時段到季節)的風景、使用密度與強度,各自及綜合對應到不同的使用情境與規模。「留白」成為動詞,形成動態變化的風景。
北宋汝窯:優雅而謙懷
「方圓之間天地闊·浩浩蕩蕩大氣闔」搭配青瓷藝術家㚕磬仿北宋汝窯作品,投影在會議室。高承恕董事長希望建築意象擁有優雅而謙懷的氣質。隈研吾先生看著投影,揚起微笑,不斷點頭,了解,同意。當天也致贈隈研吾先生一件㚕磬窯作品。這一份紀念品交給事務所同仁帶回東京,因為隈研吾先生個人下一站是歐洲。整個案子安排隈研吾先生的行程,只有少數幾趟是東京臺北的來回機票,通常都是單程機票,往返於不同國家。有一回餐桌上隈研吾先生解答大家的疑惑,對於如此緊湊密集遍及全世界的工作模式,還能夠寫書?答案是:「書都是在飛機上寫的」。結果這個青瓷紀念品,擺在我的後車廂,大家都忘了,自己也是幾天後才發現。隈研吾先生接續幾趟單程機票回到東京事務所,就問起:「青瓷在哪裡?」日後從東京端來的概念模型,還真有留白、汝窯的味兒。

人才是主角
前紐約市都市設計總監Alexandros Washburn在一場TEDx對於城市的公共空間完美定義:
"Public space is where citizens meet as equals, where society builds trust."
「公共空間屬於市民(使用者),平等相處與共享,社會同時在此建立互信。」
我們認同也相信,這是校園場域應該彰顯的核心價值,校園的空間改造及新建工程,都是秉持這一套原則盡力實現,在屬性不同的場域裡,因為共享,相互尊重、相互觀察、相互理解,公德心和新的啟發,同時融入生活。共享的學習、生活及工作空間,是如今的program組合。校長室沒有搬遷至共善樓,室內配置沒有框出專屬的院、系使用。我們希望每一位在校生都有在共善樓上課的機會,公共空間開放全校師生同仁使用。
人與人、面對面的互動,我們相信存在著無可取代的價值和意義。正式與非正式的學習分享場域、社交場域,都有值得珍惜的面對面溝通與相處。共善樓室內的配置,擁有門牌的教室面積和社交公共空間,大約是1:1的比例,因應不同模式的面對面相處。基地無圍牆,與既有校園和城市,完全步行串連。基地內也沒有車輛迎賓落客區的設置,但是目前偶爾還是需要藉助移動花台和柵欄,傳達校園周圍和校園內四米至八米寬的人行步道不是汽機車的停車空間。我們也是親眼看到才相信,就是有車輛大剌剌地順著無障礙順平,沿著硬舖面開上來停車。畢竟尊重人行空間及遵守交通規則的國民素養,是教育議題。
合奏和鳴
人與人的團隊
隈研吾建築都市設計事務所(KKAA)在合約上,負責建築主體概念、景觀規劃概念、主要公共空間室內設計概念。最終方案可以地景建築形容,室內、半戶外與景觀的密切連結,地下室也不像地下室,一樓也不是真正的一樓,屋面延伸連結地面,室內lobby、走廊、社交空間也沒有明顯分野,因此,設計工作的內容其實包涵上下裡外,相當充實。過程中KKAA團隊有一位至兩位臺灣同胞,溝通以英語和中文並用。校方團隊,由建設規劃及營運管理辦公室主導,負責監督及協助整個案子從零開始到最後收尾及滾動式的改善。設計規劃面向由建築專業學院師長負責校內重點空間改造及新建工程,共善樓是逢甲大學64年來規模最大的建設。主要再加上總務處、財務處、資訊處密切配合,其中還包括邀請校內師長團隊提供相關專業協助:智慧建築、低碳建築、室內聲學分析評估、3D列印室裝傢俱、街道傢俱製作(建築專業學院)、交通影響評估(運輸與物流學系)、大地排水計畫(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
營運管理同仁在籌劃初期就編制到位,共善樓的環境及空間維護是無法藉由傳統定時掃地、拖地和倒垃圾就完事。遵循隈研吾先生的設計意圖,選用的室內裝修與傢俱均為淺色系,清潔維護的力道,打第一天起同意設計,就知道需要更費心力。打掃之外,配合多元使用配套的傢俱及設備調度、傢俱設施的維護保養、無圍牆開放校園的保安門禁監控,整套的物業管理邏輯,都需要跳脫以往熟悉的模式與習慣,因此在設計先期,管理單位就參與討論和設計,一起研擬,一起為日後的實現暖身。
在地建築團隊及監造單位,由技聯組工程顧問為班底的欣祥工程顧問和陳立權建築師事務所負責。在地設計單位的參與也是和KKAA合作初期就加入,所有合情的設計討論,始終都顧及合理、合法的層面。逢甲校方這一份委託,除了擁有與國際事務所合作經驗,希望工作團隊身處臺中,能夠面對面地溝通,至關重要。同時因為在地,對於公部門的要求與行政更為熟悉,有效控制時程及工作的效率,光是趕著發函用印,就慶幸我們在同一個城市,若需要坐高鐵,時間的成本就是另一種負擔。因實際需要參與不同屬性與主題的會議,我們曾有和在地建築團隊一週見面四次的紀錄。若配合的事務所不是在臺中,還真難辦到。

施工團隊由麗明營造承攬。曾經一時共善樓的人員編制是麗明規模最大的工務所,不是因為工程規模最浩大,也不是造價最高,而是我們選擇實現的空間幾何,需要眾工種們繁瑣的整合與協調。同時配合學校的運作,需要把握寒暑假後開學的節點。實現設計的旅程相當漫長豐富,也緊湊到極致,協同上述提及的團隊,大夥著實花了一段時間和不少力氣,才整理出一套非一般建案的合作模式,從觀念的調整,到設計意圖的理解與貫徹,再加上對於品質的要求拿捏,都是同心協力的過程和結果。本文後續將繼續分享「合作模式」。在2024年1月,校方、設計單位和施工單位,組團赴東京看建築,實際參訪隈研吾先生作品。不難想像,這一團的行程,就常常出現一堆人蹲在地上,圍繞著一個牆角討論施工和材料細節,看什麼做得好,如何可以更好。對於設計意圖的理解更扎實,同時也建立要超越的企圖,就算是被冠上「有夢最美」的形容,也值得。這一趟旅程朝夕相處建立的革命情感,的確成為日後合作的關鍵與共同語言,這也是人與人之間的故事。
大家最好奇的問題應該是與KKAA隈研吾先生團隊的合作經驗,先簡短回答,是「愉快的」。愉快合作的基本元素是「互信」,因為價值觀相同,因為相互理解,經過溝通而取得設計意圖與使用需求的平衡是實現的共識。KKAA是容易溝通的團隊,對於業主的需求,相當看重,若是預算、造價、材料、功法上的問題,就直說,然後大家一起想辦法。由於首次合作,在初期階段,曾經碰過在地團隊因為非常尊重設計概念,將隈研吾先生的圖說被視為近乎「聖旨」的狀況。校方也有明確的立場,因為最終的使用和維護管理在校方,所以final say是屬於逢甲大學。
我們建設規劃的夥伴們此時就扮演溝通橋樑的角色,了解雙方的出發點,在察覺設計意圖和最有效率的維護管理有出入時,若是設計意圖的場域感能夠帶來的價值是值得/難得的,就會投注更多的維護與管理資源;若付出的代價或影響遠超越校方的預期,就必須收斂調整。況且KKAA已經表明開放溝通的態度,那就好好商量。KKAA內部的工作模式也注重面對面的溝通,每一個案子都要掛號排隊Kuma check,設計的決策,需要當面和隈研吾先生報告和確認。因此我們許多往返的溝通,也圍繞著Kuma check的時程,隈研吾先生在東京辦公室的時間,可以想像那一份緊湊,所以我們在臺灣,也盡力協助將提出的調整和問題做到精準,壓縮往來的作業時間。順道一提,隈研吾先生和事務所同仁的溝通,自從學會使用手機上的LINE,就成為了一個無時差的境界。
近幾年,隈研吾先生在臺灣的建案增加,來台的頻率也增加,所以我們也藉機安排我們的Kuma check。一般工地對於設計方常會有「不要讓建築師知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刻板觀念。講理的隈研吾先生,提出的意見和想法都有所本,非自我主義作祟,所有提出的問題與議題,都是為了更好的結果。過程中,以試做和mock-up的討論模式最有效率。第一次的mock-up,包括鋼構、玻璃帷幕、屋簷倒吊板、地坪。帷幕外側的豎向格柵,一面是熱轉印紋路的鋁板,一面是實木。因為處於戶外,所以當時KKAA同意使用耐候教佳的非洲柚木,隈研吾先生在現場說:「喔,非洲柚木的顏色在陽光下比想像來得深」,於是請同仁拿色票,重新選樣所有室內顏色,從白、灰改為大地色系,配合非洲柚木。在現場的施工與設計團隊們,集體倒抽一口氣,現場幾乎真空⋯⋯因為我們已經花了很大力氣,統整完成鋼構防火面漆、室裝隔間、防火門、消防栓箱、機電櫃體,若再重新再來一輪,將直接影響工期,茲事體大。時候經過校內會議、設計工作整合會議及工務會議,決定將非洲柚木更換為成色較淺的日檜,維持原面漆色彩計畫。

當使用需求與設計意圖衝突時,該聽誰的?
還是如此提問,根本不對?尋求解決方案的路徑,應該先了解兩者的價值觀,是否需要重新審視「視之為當然」的價值觀?「視之為當然」是否需要被挑戰?我們以435席的大講廳,生日堂舉例。先滿足大家對於「生日堂」冠名的好奇心,由來是感謝熱心校友,捐贈大講廳的室裝費用,校友父親名有「日」,母親名有「生」,於是「生日堂」,以表感念。講廳內,三面有窗,雖非創舉,我們勇於嘗試。內裝牆面由隈研吾先生指定並客製色彩來自丹麥的Kvadrat吸音板,3D的造形也是客製研發的系統,吸音板和屋頂之間,就是視覺穿透的玻璃帷幕,與其他立面一致。舞台背牆和兩側,都是以天空和樹梢作為背景。舞台坐北朝南,白天陽光所製造的光影,在不同的季節與時段,營造不同的戲劇性。Everything has a price.代價是因為自然光的直射而影響投影效果。
經過幾番討論,有將投影改為電視牆方案,或加裝遮光窗簾降低直射,也考慮透過電控玻璃遮光。電控玻璃因玻璃尺寸及貼膜的維修難度而作罷。討論過程中,引發了重新思考基本問題,而不是圍繞著技術問題,討論的重點不應該是「電視是否看得清楚?」而是舞台上是誰?分享傳遞的內容是什麼?真正有料的講者,是不是沒有PPT也能夠吸引觀眾,互動、吸收、思考、收穫?是的,我們又回到「人」的故事,講者不是躲在陰暗角落,讓PPT成為最明亮的主角,主從關係建立了共識,我們再評估不同方案。
若採用電視牆,就必須落地架在舞台面,取代部分背牆的吸音板,形同婚宴會館。當沒有播放畫面時,就是一塊黑色矩形,就整體觀眾視覺的空間比例極不協調。吸音板的系統也無法改造成為活動屏風,遮擋沒有在運作的電視牆,這是電視看得清楚需要付出的代價。以空間視覺比例作為考量基礎,首選是400吋的捲軸銀幕投影,面對自然光的影響,決定以流明數相應對。我們請廠商在學校體育館實際模擬,以兩台2萬流明,疊成4萬,效果還能接受,但是接受得很勉強。亡羊補牢,決定在西側加裝固定窗簾,雖然選用擁有少許視覺穿透的窗簾,跟設計相關的團隊百般不願意,因為從裡、外都會看到窗簾,就是這一道帷幕牆長得和其他不一樣。由於超過7公尺長度,當時沒有廠商敢做捲簾,所以必須接受固定窗簾的存在。
有一天,在生日堂施工現場,看到一位沒見過的工班在講台上走來走去,不時抬頭看帷幕,看屋頂。上前請教,原來是窗簾廠商準備丈量尺寸。抱歉,懸吊鷹架,昨天拆了,現場也沒有16米的高空作業車,所以沒得丈量,您來晚了。當時自己心裡默念「天助我也」,因為工期趕,就名正言順先不裝窗簾。只有試試看,若真的不行,就再說。結果⋯⋯室裝完工九成試用時,真的、真的、真的不行!上午東側,下午西側太陽直射,徹底擊潰4萬流明。啟用典禮就硬著頭皮,在風和日麗陽光普照的狀態下,隈研吾先生的PPT漸漸的被陽光侵蝕,演講中途改為投影在舞台兩側的85吋屏幕。隈研吾先生也沒有介意,反而超愛光影效果,沒想到陽光和吸音佈的色澤如此相得益彰,絕配。

畢竟這是我們自己看得舒服,若日後出租場地,承租者很在乎投影要看得清楚,還是必須要想辦法。就在傷透腦筋之際,輾轉得知一間捲簾廠商有適合產品,也有意願施做,經過幾輪的協調,確認固定方式及電路,再搭鷹架施做東、西兩側。大家都開心,效果滿意,需要遮光就放下,不需要就收起。但是,很悲劇的「但是」,實際的空調的氣流會造成捲簾輕微搖擺,這是拆了鷹架之後才觀察到的現象,雖然輕微,但是超過7米的擺動就是問題,結果第一次上收的時候就有幾樘出現偏移,其中一樘直接攪到滾軸卡死。解決辦法,30樘捲簾重做,調整寬幅,多給一點tolerance,並加裝導引鋼索。是的,我們又搭了一次鷹架,希望是一勞永逸。
設計工作整合會議,面對缺工的現況與未來施工階段,麗明營造承攬了隈研吾先生臺中巨蛋工程,巨蛋團隊前來共善樓工地請益。共善樓團隊不約而同提供的建議就是:設計工作整合會議(有別於營造單位主持的「工務會議」:聚焦討論進度與缺失改善追蹤及工班工序協調)。共善樓建築本體斜來斜去的幾何造型搭配界面銜接,就是繁瑣,而且赤裸,沒有修飾掩蓋的機會,基本上只有廁所有配置天花板,所以要能夠達到設計意圖的完成品質,跨工項的橫向整合是重要關鍵。
觀察到在地工項的工作習慣,就是做到顧好自己就好,把自己的圖畫出來,交給麗明就好,當碰到細部施工圖shop drawing不夠嚴謹,考量不夠周詳時,多半下場是在現場亡羊補牢,死馬當活馬醫,不斷拆彈,很難全身而退,多少留下遺憾。於是校方團隊提議每週召開「設計工作整合會議」,由營造總包每週召開,施工承包廠商、設計單位及監造單位出席,校方列席,會議重點:以shop drawing細部施工圖作為討論和溝通依據;會議是以面對面的方式進行,依據階段和需要,設計人員和施工人員分開或共同出席;相關的工項彼此了解工序、所需工作空間、保護措施、施工/安裝尺寸容許的彈性與調整機制。所以各自進行的shop drawing是我的圖中有你,你的圖中有我;期望是落實按「深思熟慮的」圖施工,預防而不是衝突出現再檢討。
我們將設計工作整合會議分為A和B兩大組,視需要跨大組出席。A組:鋼構、玻璃帷幕、複層屋面及屋簷倒吊板;B組:室內裝修、機電。總計A組召開超過60次會議,B組也將近60次。成效最理想的狀況,以A組為例,當帷幕系統確認可以消化鋼構公差之後,開出來的基準線,可以在現場與後續工項共用,也可以成為廠內預製的尺寸。或是帷幕系統的收頭構建多一個折角,接續三明治板只要頂著折角安裝,就自然是一條對齊的界面,因為帷幕的精度就是直線的保障,所以廠製的折床多折一道,省下三明治板開線和逐個對齊的安裝時間,多折的這一道,再offset出去多少,就是倒吊板底部的基準線,省去重新開線、安裝和拆卸假固定,因此縮短單項的工期,提早騰出空間和拆架,總體來說是划算的。
一套好的shop drawing帶你上天堂的觀念,是本人在紐約從事帷幕工程時被灌輸的生存之道。在美國,當建案是工會工地時,現場的工人素質就幾乎不可控,除非能夠有不間斷的工地來「綁定」或「養工班」,不然很難培養和主動幫你解決工地狀況的夥伴,對於工會工人,多做一天就是多領一天工資,職業倫理差一點的工人,就希望你的材料出錯,然後一邊坐在工地等你修改,一邊領時薪。真正要趕工,就依據工會規定,兩倍、三倍的加班費。若是碰到跨州的建案,那就完全任工會工班宰割。所以,細部施工設計的最高境界就是只要鎖螺絲就完事,用不到多少智商,現場不切割、不焊接。細部施工圖最好能夠畫成IKEA或是LEGO的說明書。
所有需要的智慧,都在自己廠內預鑄製成,現場單純組裝,將工人工藝的要求將至近乎零。能達到如此理想境界,關鍵是單元化系統,而系統的要件是清楚認知哪裡是死也要對準的角落/尺寸,哪裡是留著調整的活路/機制。首先了解設計與現場尺寸的出入,能克服現場誤差,完成原始的設計尺寸,最好。若做不到,能做到什麼地步,就說/畫清楚。依據同意的尺寸,竭盡所能,在廠內製作,畢竟在工作台上切割、焊接金屬要比在鷹架上有效率,也漂亮。既然預鑄,在工廠確認單元的組件都達到精度要求,廠內試組,自主品管核可,拆卸上車運送至工地,到工地就是將單元再次組裝。安裝方式也是細部設計重要環節,用吊車、用省力滑輪、用千斤頂、用人扛,相應的配件也納入廠製,或是客製安裝吊床,安裝時,哪個角落或是哪個構建接到哪裡,只要接上就準確到位了。系統的另一要件就是調整機制,聰明的系統,調整XYZ其中一向就足夠,就算是三向都需要調整,都還是強過現場丈量、裁切、焊接,最重要的目的是壓縮現場所需的時間與空間。我們也親眼見證,因為沒有系統,安裝時角落是否能夠準確銜接,被視為一場賭注。萬一對不到,再看怎麼辦,結果下場是整排拆,重新生產,再安裝,其實都是碳足跡,時間也是最要命的成本。
最後一點,我的工頭恩師教我,「多做一點,是買保險」。自己要清楚相關的工項和工序,需要提醒工序在我們之前的工班,該做準的,該留出的空間,都在shop drawing裡標清楚,讓我們工作順利。我們系統若能夠照顧到接續的工班,就給他們方便,因為他人的錯誤很可能會牽連我們,最終仍是划不來。他人好做,我們也好過,大家都好的真理,煩請參看優質shop drawing。
以上就是對於缺工現況與未來的建議,從提升設計端著手,把握有現場經驗的師傅和工程師,一方面指導設計單位,朝系統化廠製思考;一方面與營造端橫向溝通,讓shop drawing到位。現場則以組裝為大宗,手藝好的人才,只專注在關鍵的節點。最高段的細部施工圖shop drawing,就是直接將檔案名改為「竣工圖」。
繁花自開
共善樓這一趟奇幻旅程,藉由這一篇分享,沉澱回憶,發覺累積了不少故事,若大家想聽,再慢慢道來。所有故事的背後,都是感激。謝謝每一位投入的夥伴們,也許有些不自覺,都是為了教育的理想盡一份心力,共同打造了水湳經貿園區最低矮、最綠的、陽光最溫暖的場域,我們在此的學習、生活與工作,為了追求和實踐更好而提問,並且找尋答案,有屬於個體的問與答,有屬於群體的問與答,每一輪的問與答,每一輪的嘗試,每一輪的不同,就是成長的累積,讓我們的視野更廣,心胸更寬闊,過程的體驗和記憶,也許多年後才會發酵,成為支撐我們改變世界,讓世界更美好的動能,百年樹人的時間刻度是寬廣的。這是妄想還是理想?會說是妄想的,不妨嘗試跳脫KPI和坪效的邏輯,就可以更接近理想,同樂.共善.大好。


*本文資料轉載自 建築師雜誌 │ TAIWAN ARCHITECT Magazine │ 2025/10
分享:
相關消息